- 当前位置:k8凯发-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 > > k8凯发-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
- 品读扬州
苏北里下河纪事
发布时间:2019-8-20 9:47:05 作者:吴建宁 浏览量:1516 【字体: 】
这是一本怀旧的画册,只言片语叙说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一些往事。那些曾经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的知青,那些沧桑的木桥和岸边的村庄,还有运河里那些老旧的机船……,作品语言直白,简洁,描写的内容也如大地般朴实无华,画面中没有绚丽的色彩和动人的旋律,有的只是一种宁静和画面深处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忧伤。作品已不再是局限于里下河地区的地域纪事,它已是一个宽泛的时代记忆,它是对那段曾经“激情燃烧”岁月的思考,它是一段深沉的乡情,它也是那辈人几十年来无法抹去的情怀……。 ------老路
刚插队时村口有一座破旧的木桥,是村里通向外面世界的主要通道。走在晃晃悠悠的木桥上脚下还吱吱作响,桥板上坑坑洼洼的很是沧桑。村里人家的婚丧嫁娶,挑米辗稻,进出村庄都从桥上过。多年来这座桥承载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和村里人的辛酸苦辣,多年来这座桥也见证了村里的人世沧桑和时事变迁。
后来这座木桥因实在不堪重负被拆了,修了座水泥桥。
那时我们插队在苏北里下河地区,在大运河的东面,因地势低洼,故称里下河。那里河网密布,交通运输主要是靠人撑的木船,我们当初来时就是生产队用木船把我们撑到了庄子上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那里还很贫穷,社员住的都是茅草顶的土坯房。我们来后队里也给我们盖了一间土坯房,但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,在当时这就是比较好的房子了,称为“四角硬”。
队里的社员对我们都很好,他们为人很善良,那时每家的口粮都不够,而我们又不注意节约,常到青黄不接时没吃的了,我们常会向家前屋后的借米借油,尽管那时他们是一家几口也缺吃少穿的,但是仍然会借给我们一、二斤米,小半碗油。这些现在几乎是谁都没眼看的东西,但是在那时这几乎就是在借命啊!至今想来眼框都会湿的。
多少年了,忘不了他们对我们的宽容,忘不了他们对我们的照顾,也忘不了他们吵架时的那种互不相让、上房揭瓦的气势。他们吃苦耐劳,敢做敢当,敢吵敢闹、敢恨敢爱……这就是我们苏北的农民,也许这也是中国广大农民的缩影。
我们刚来时,村里的小店是在当时的大队部里,这里是全村庄最好的砖墙瓦房四合院,店里卖些农民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和小的农具,如要买比较好的东西,大多要上临泽镇了。记得我常在这里买“山芋干子酒”和八分钱一包的“经济”香烟。那时当地最好的香烟可能就是“大铁桥”了。那年有个在子婴河插队的知青到我们这来玩,吃饭时他说到:他和生产队里的社员喝过“钉子酒”,就是一瓶酒一个杯子一个锈钉子,每喝一口酒,就把钉子在嘴里吮吸一遍,喝酒没有菜,就把锈钉子的味道当下酒菜了。这还真没听说过,不过在那个年代,这种事也是有可能的。小店晚上点的是罩子灯,比一般人家亮多了,所以晚上常有人在这里抽着旱烟三三两两地说闲话。那年月抽的也就是干树叶摻和着烟叶,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,他们说这是“扯焉子”,也就是混时间的意思。小店到了晚上是要上门板的,门板上还依稀可见西一,西二,东一等毛笔字。
后来村东头盖了供销合作社小店就没有了。
那时庄子上有两个生产队是女知青,她们比男知青多个苦活就是插秧,好像四、五月里就要开始插秧,天不亮就要起来烧早饭,等一切忙定天也亮了,斗笠一戴裤腿卷的高高的就下水田了,从早晨下田插秧直到天黑收工,几乎一整天都在水田里弯着腰插秧,遇到刮风下雨,就用一块塑料布往身上一披就是雨衣了。水田里常有蚂蟥,那是一种吸血的虫子,叮在腿上就下不来,等发现了把它拽下来了,伤口还会继续流血,要好大一会儿才会慢慢止住。所以只要下水田干活,都要时不时的看看自己的腿。一天插秧下来,天黑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,她们说腰好像要断了。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种田是很辛苦很辛苦的。那时我们队里有五百多田,大多是种双季稻的,真是一年忙到头,春节小年刚过就开始犁田、耙田、育秧、插秧、薅草,然后收割、脱粒、晒稻、翻场。再然后晚稻从七月份开始,又把早稻的农活再重复一遍,直到十二月晚稻上场。冬天还要外出上大型(大型水利工程)挑河工,下河罱河泥、挖草粪塘、开沟挖墒等等等等,接着就过春节,这才能歇几天。小年刚过又开始犁田……。年复一年,农民们整年忙的都没时间看病,当然也是没钱看病。村上虽有合作医疗,但也就是看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,那年头缺医少药,所以农民们小病就扛,大病就拖。农忙时刚收割的稻子一上场就要连夜打稻脱粒,一天睡不了几小时,连续几天下来,人都累的迷迷糊糊的,为抢时间做饭,就胡乱的打一锅稀面糊吃(青黄不接时有点面粉打面糊吃就很好了),撒点盐搅和搅和喝上两碗,碗一丢立马出门继续干活,晚上回来已累的不想动了,盛点锅里中午剩下的面糊吃,盛到快见底时才发现锅里有东西,捞起来一看是一条长长的抹布。
我们知青这一代人,有了在农村历练的这碗酒垫底,在以后的工作中,什么苦事难事我们也没怕过。我们继承了农民吃苦耐劳的品质,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地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。在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知青的血染成的。
牛在农村是主要劳动力,耕田钯地,辗稻打场都少不了它,所以社员们对它们呵护有加。冬天牛在牛屋里好吃好喝,天冷了还烧火取暖,还有人睡在那里陪着它,夜里还要喂料,还三天两头地往牛嘴里灌香油,很是令人嫉妒。冬天冷的时候我们还会钻到牛屋里沾牛的光,那里暖和。
那年月农民要操心锅里的米,还要操心锅下的烧草,锅上锅下少一样都要挨饿。我们到了队里,烧草成了问题,我们锅上有米(当时好像国家供应知青半年的粮食),但锅下没烧的,生产队便决定我们烧牛草。所谓牛草就是稻草,是牛的饲料,那时牛过冬直到来年的早稻上场,饲料全靠牛屋前的大草堆了。我们烧稻草就是烧牛的饲料。那时我们还不知节约,常拔很多的牛草回来烧热水洗脸泡脚,而社员们只是用大灶上靠大锅边的小铁罐子里的那一点热水(当地称之为“罈罐”),罈罐里的热水是烧饭时温热的。社员们是很少专门烧热水用的。我们那时随意的烧牛草,太奢侈了。现在想来还很是慚愧。
我们插队时村上还没有通电,社员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墨水瓶里面灌点媒油或柴油,上面有个园的铁片盖住瓶口,园片中穿个小铁管,中间再穿根自己捻的粗点的棉线做灯芯,这就是灯了,栓根绳子挂在墙上,蚕豆大小的火头还冒着黑烟,灯点的时间长了,第二天起来鼻孔里都是黑的。条件好的人家,晚上点有玻璃罩子的媒油灯,这种灯亮而且不冒黑烟。那时我们点的就是罩子灯,我晚上画画所以睡的晚,一晚上要点一灯煤油是用二个鸡蛋换的。
那个时候农村的交通落后,汽车很少,等班车也没有个准头,好在那时有二轮车,也就是二八永久自行车后面货架上捆绑一块长木板,可以带二个人,倒也方便。骑车人技术很高,等后面二个人坐好后,大喊一声“别动了”,推着车就跑,然后一脚狠蹬一下地面迅速抬腿绕过大杠坐稳。技术娴熟,整套动作一气呵成,令人叹服。
半个世纪前,运河大堤的公路上跑的公共汽车,那时车顶上装好货后,就用大网子罩住拴结实了,才开车。有时开到半路上,发动机熄火了,司机就要下车,拿出根铁的摇把插进发动机里摇,司机摇累了机器还不响,这时就有乘客下车来自告奋勇地接着摇,直到汽车发动。车上的乘客也司空见惯,也没什么怨言。那时的人很宽容。换到现在,又是投诉又是赔偿的,现在的人反倒不宽容了。由于当时的路面状况不是很好,好车子跑几年,也就成这样了。
画面中画的是邻县高邮的界首镇,这是大运河边的一个镇子,因地处高邮、宝应、金湖三县交界而得名界首。这个镇子在大运河的河堤旁,也是一个千年古镇。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界首镇离我们双琚较远,插队十年我只去过两、三次,感觉很破旧,好像就一条街。因为界首在运河边,所以界首码头也是大运河里南来北往重要的水陆码头。
大运河中的客货混装的小班轮,主要作些短途的客运和货运。当然也可以直接抵达扬州港或镇江港。票价比汽车便宜。
这是家乡的夜景,冷冷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,村庄静悄悄的笼照在月光下,安详而充满神秘,令我神往。这是我画中的“家”,是我心中的“家”,也是我永远回不去的“家”。
多年来心中积累了很多话,一直想说出来,今天终于说了些出来了,如释重负。画面和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点往事和感受,记录了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,也记住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曾经善待过我们的农民。今天国家富强了,当我们回首,曾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付出时,一切便也释然了。
这是当时运河里的小火轮,它能拖着三、五条或更多的那种木头的货船,在运河里跑运输。我们当时就是坐着几条货船,由小火轮把我们从南京拖到宝应的氾水镇,好像再分到小船上拖到夏集,然后再由各大队的船带走直到生产队的。五十年前的事了,也只能依稀记得了。
我们刚到农村,我们对一切都感到新鲜,但是对一切又很无知。当时生产队是撑船把我们接回的,船快到庄子时,只见远处的天底下,是一大片灰蒙蒙的草屋,环顾四周一片沧凉,河两边一眼望去很远的天边有点树影,周围一片死寂,只有船在水中前进时“哗”“哗”的划水声。心中顿生悲凉。到了庄子后,看到社员们穿着打了很多补钉的衣服,再看着那片低矮的草屋,不禁困惑。还以为像电影中的一样,社员们都穿着新衣服,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……。和想像中相差太大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自己一直很徬徨、迷茫。我是属于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那部分人,所以平时只知道埋头干活。干着干着“一不小心”干成了个“学毛选积极分子”,还和我们庄子上的另一个女知青,一同参加了“宝应县知识青年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,开了这次大会后,“长了见识”,学习了“新思想”,回村后也大概地知道了,今后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在这片贫脊的土地上。
刚来到苏北平原,田里还有大风车。风车转动带动水车翻水灌田,大风车转动时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,我们队好像有两架大风车,那时生产队里还有人踩水车灌田的,人站在水车上踩,那是要点技巧的,不会踩就会就掉下去。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五百多亩田,是全大队最多的,最远的是凌田,人走到田里干活几乎看不到庄子,所以我们那时下凌田干活都要带中饭,中午不回家。凌田做活是很苦的,尤其是夏季稻田薅草,连找块阴影休息一下的地方都没有,任由毒辣的日头爆晒。一个夏天能脱皮两三次。一马平川的苏北平原就是在冬天刮起北风来也是肆无忌惮、无遮无挡、凛冽刺骨。
那时农民的生活的很苦,口粮不够吃,干活时每天可以烧顿干饭,如遇雨天不上工,一天最多也就吃二顿稀饭。那时要上交国家一定数量的粮食称之为“公粮”。上交的公粮都是上好的稻子、麦子,而那些颗粒不饱满的不好的我们称为“下脚稻”的粮食,则留下分给社员作口粮了。中国的农民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忍辱负重、辛苦劳作用自己的勤劳和付出支撑起了整个国家。
我们家共五个人,都是同班同学,就组成了一家。那时刚插队,我们吃粮国家还是有保证的,有时吃不了还有节余,日子长了余粮也就多了,社员粮食不够吃,我们粮食还多了不少,于是就想出了餿主意:卖粮换钱。这在当时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,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全国人民都吃不饱,你们胆敢卖粮!当时我们撑了条船装了两大筐白米出了庄子,直奔临泽(是十多里外的一个镇子),后来队长顺着大河堤一路追来才把我们截住。后来是大队,小队对我们教育,再后来粮食怎么处理的我记不得了,只是记得后来没处理我们。
那时我们年轻,太不懂事,地里的活干不好,却还相互打架,偷鸡摸狗。当时村上农民还很贫穷,经济上仅靠年底队里的一点分红,是远远不够家里一年的生活开支的,柴米油盐、日常用度。所以,一般农户还指望家里的鸡下蛋,拿到村头合作社里换点媒油、换点盐、换点其它生活用品。但是这些下蛋的鸡却给这些“挨千刀”的知青偷了。他们对我们是痛恨有加。那时我们偷鸡前就要烧好了一锅水,鸡被夹在棉袄中带回来后,立马热水烫、拔毛、开膛破肚、下锅大约十分钟左右拿出来,这时鸡肉最嫩,再煮就老了。然后麻利地切鸡,开吃,也就几分钟桌上就剩一堆骨头了,报纸一包扔了。出门后像没事人似的。我们以为没人知道,其实社员们在田里干活时就知道到了,知青家烟囱冒烟了,不知哪家的鸡又没了。因为上工时庄子上是不会冒烟的。我们只是掩耳盗铃罢了。为此社员从小队闹到大队,而那时大、小队干部也是多偏袒我们,所以也就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,我们真的很深很深地伤害了这些贫苦的农民。可是当我们有困难时,社员们仍然会帮助我们。队里派农活时还是会把轻活派给我们。他们的大度和宽容至今都令我们无地自容。
今晚邻村大李庄放电影。这消息不径而走,大家听说后都很兴奋。到下午时庄子上各个队的社员都无心干活了,巴望着太阳早点落下去。我们干脆提早收工,匆匆回家,赶紧挑水、淘米、点火做饭,今晚要烧干饭,因为来回要走十几里路呢。就着一点腌菜吃完饭了,门一关拔腿就走。门也没锁,其实锁不锁都是无所谓的,那会儿民风好。出了庄子看见往大李方向的田间小路上早有人急急地往前赶了。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,一年能看场电影已是很好的事了。平常哪个村子放电影,周围十里八乡的社员都要去看的,人们都穿的干干净净的,大姑娘小媳妇们是要打扮一下的。天擦黑我们才赶到,电影已开场了。只见幕布前后都是人,其实前面看后面看都是差不多的。那会儿还没通电,放电影的都要自带发电机的。只听得远处的船上发电机“嗵、嗵、嗵”的响,一根粗皮线连到一张桌子上的放映机,桌腿上绑根竹竿,上面挑个小灯泡照着放映机,桌边还围着一圈小孩,后面还有张桌子,另一个人在倒片。前面的银幕是二根粗长的竹竿埋在地下,银幕就栓在两根竹竿中间绷平,竹竿上捆个大喇叭。我们就在银幕后席地而坐。今晚放的是“上甘岭”和“永不消失的电波”两部片子。那时革命战争片子是很收欢迎的。当银幕上的新闻片头结束正片开始后,吵杂的场子顿时安静下来了,人们都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看着银幕,在电影播放中,有时大喇叭还会插播一下生产队领导班子开会的通知。人们对这并不在意,大家的情绪随着电影里情节的起伏,时而高兴时而稀嘘。随着电影的播放,夜已渐深。电影放完已是快十一点了,散场后人们各自回了。漆黑的夜晚,远处田里不时有电筒的灯光,忽闪忽闪的像天上的星星,大人小孩意犹味尽地谈着电影里的情节,嘻笑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。
那种来回跑十几里路看电影的感觉,那种单纯而简单的快乐,现在再也没有了!
有年冬天特别冷,春节快要到了,我因没钱就不回家了。我们家的两个知青准备回南京过年,那时我们回家都要带点年货的,队里养的鱼或田里种的茨菇。那年他们准备了两纸箱子鸡蛋,这个在城市里也是稀罕货。好像是因为雨雪天,汽车不通,他们便到邻县的沙沟镇,准备坐船到镇江,再在镇江坐火车到家。那时交通太不方便了。他们到了沙沟,没想到天太冷了大河结冰,船也不通了,想回来路也不通,结果他们在沙沟那个小码头窝了三天,因没钱吃饭,就找了人家帮忙煮鸡蛋充饥。后来总算到南京了,可能年货鸡蛋也吃的差不多了。
这是那个年代内河里常见的小班轮,也是客货混装,沙沟码头在那时也停靠这种小班轮。如果那年沙沟水面没冻住,他二人就坐这小班轮到镇江了。
我们里下河地区,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,这一带的老战士很多,我们那时都喊他们为老革命。他们大多是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,胜利后也许因为没有文化或其他原因,又回到了家乡。那年头国家也很困难,还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些老兵。当时他们还很穷。每到年关,有很多人都是要出去跑年(要饭)的。所以每到过年,各村大,小队干部都很紧张,每年按上面指示要制止老革命跑年。我们庄子上就有一个老战士,我们叫他老艮,他曾和我们说:当年新四军打兴化城,架梯攻城,被敌人剁下来的手能用箩筐装。可见当时战争的残酷。每到过年大队里再怎么困难,也要给老艮一点米、油和几斤肉,让他过个饱年。
我们干活时间长了,就想到临泽镇子上去玩玩。吃顿饭解解馋。我们一般早晨起来吃过早饭后,要等到社员们都下田了,我们才出门。那时庄子里已静悄悄的了,颇有点“鬼鬼祟祟”的感觉。我们出了庄子上大堤,过了匡庄就顺着河堤往前走,大约十里左右,就远远的看见河上有个没有栏杆的木桥,桥下停了很多大小船只,不断的有人在跳板上来来去去的上货下货。过了木桥便进了镇子。这是个千年古镇,历史上曾是高邮县的三大古镇之一。镇里三街九巷,交通畅达。古来曾是商贸重镇。上世纪六,七十年代的临泽虽已无往日的繁华,但仍是这方园数十里的商业中心。镇里街面不宽,窄窄的街面中间一条青石板小路,两边是商铺,店家,日用百货,饭馆粮行,那时店家都是上门板的,跄在街边的门板上用毛笔写着数字。店里的柜台和墙上的立柜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花绿绿的商品。街面上人来人往,带草帽的、挑担扛包的等。这都是附近的农民来买东西或办事的,来去匆匆。这场景不禁使人想到电影“林家铺子”。玩了会儿几近中午,找家饭店吃饭,那时饭店里的地面大多是青砖铺地,打扫的干干净净的,店里几张四方桌,每边一个长条凳,落坐后,一个人去交款处点菜付钱,交完钱后,顺手在旁边柱子上的筷筒里抽几双筷子。菜上齐后,拿起筷子夹在腋窝里来回抽几下,算是楷过筷子了,然后就不客气啦。几瓶啤酒下肚饭菜一扫而空。吃过后再在镇子上逛逛,太阳西下时就回了。每次吃饭都少不了把饭店里的筷子、小勺子、小盘子吃回家。
这是常年在内河里跑运输的的水上人家,这些人长年以船为家,这种机动船也为临泽镇,沙沟镇,三垛镇等里下河地区的各个地方,运输日用百货和农用物资。那时公路交通不发达,路面状况不好。水运装载量大而且成本低。所以这些机动船是当时里下河地区的运输主力了。
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,田地里基本上也没什么活儿了,一年里也就这几天能闲下来。庄子上开始忙起来了,家里的女人忙着里里外外打扫,忙着准备过年的吃食,忙着洗洗涮涮,忙着锅瓢碗盏。有人家过年办喜事的,更是忙的不可开交,张家借桌子,李家借凳子,家前借碗,屋后借锅,日子过的再苦,年总是要好好过的。条件好点的人家小孩过年能穿件新衣裳,一般人家也就穿件干干净净的,补丁少点的衣服。姑娘家没新衣服的也总是要把头梳的光光的,脸洗的干干净净的再搽点雪花膏,别上几个漂亮的发卡,有的嘴上还会用红纸淡淡的抿一下。
每年春节庄子上都要组织演出,自从知青到后,我们便是演出的主力了,那时我们还演出了革命样板戏“沙家浜”,记得演主角的郭建光是我们大队星河生产队的知青。这些都已是过去的记忆了,那时我们在贫穷的苏北农村也有快乐的时候。
再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,过年每家都要舂糯米粉,还要赶在年前抢个好太阳把糯米粉晒干。所以每家都想赶紧把糯米粉舂好。那时我们队上只有一个对子,在生产队东头的一间大屋里。所谓对子,就是地上埋个石头窝窝,上面架个木头架子,支撑一根长木棍,对着石窝窝上面的木棍头上捆个一头大一头小的石头,小头正对石窝窝,木棍的另一头是人脚踩着一上一下,小石头就一上一下地砸进石窝窝里,把糯米砸碎,砸成米粉。对子是整天不停的,你家舂好他家接着舂,那几天晚上没事的社员也常到那里玩。屋里紧靠对子的墙上挂着一盏忽明忽亮的的小油灯,蚕豆大小灯头来回晃动冒着黑烟,屋里已有不少人了,紧靠对子的地上已有几个盛着泡好糯米的盆子,对子上一个人在踩着木棍一上一下的舂着糯米。屋外寒冬腊月,雪花点点,屋内人多暖烘烘的,微弱的灯光下谁也看不清谁,大家挤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的扯着闲篇,话语里夹杂着粗话和呛人的烟味,仿佛一年的辛苦全融化在这“咚”“咚”的舂米声和大人小孩的嘈杂声中。在半明半暗的油灯下,人堆里不时发出阵阵说笑声和低低的啜泣及骂声,在这里人们尽情地喧泄着一年来的坎坷和辛酸苦辣,人们心中积累了太多太多的东西,在这个晚上也毫无顾忌地流淌出来了……。 那几天我也总爱往那屋里钻,蜷缩在墙角的草堆里,听着对子一上一下有节奏的撞击声,听着粗声细语的说话声,感受着浓浓的年味,竟入梦乡…… 。
记得那时公社前面是一条泥巴的路,大路边是大会堂,当时好像是没门没窗的,里面也就是泥土地面上面摆着一些做工粗糙的长条凳子。那年头农村太穷了,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开开会就不错了。公社招开的“三干会”、“知青大会”等各种大小会议就是在大会堂招开的,这里还演出过夏集大队知青自己排演的舞剧“白毛女”。公社大路的右边是邮局,记得那时打长途电话到南京,要在公社邮局里等,等这边电话摇到南京,南京那边也要在新街口邮局等,等电话接通了再叫你到几号几号小间去接。那时通个长途电话太困难了,而今天是一部手机走天下。
明天是大年三十,中午时分,公社那条不宽的泥土路上,人少多了,苦了一年的农民也早早的歇了,都回家准备明天的年夜饭了,我被借到公社干的活也干完了,也该回家了。虽然明知回去也是一个人面对一间空空的茅草屋,家里已没米了,要借米,要洗涮多日不用的水缸,把水挑满,还要去捆烧的草,还要去买晚间点灯的油,还要……,还要……。虽然回家连菜也没有,但是家还是要回的,一个冷冷清清的家。我在公社早早地吃了中饭,就急急的上了潼河大堤往家赶,空旷的天空中偶有点点雪花飘下,大约走了个把小时,已能隐约看见灰蒙蒙天空下的庄子了,忽然又不想急着回家了,想一个人在这空旷的天地之间待着,体味这在路上的感觉,一种在不停地赶路的感觉。人在路上就有一种企盼,有一种幻想和期望。真的到家了,一切也就没有了。
人这辈子大约也是这样,在不停地赶路,“家”永远在前方不远的地方。有人回“家”可能只要几天,有的人回“家”可能要几年甚至一辈子……。人其实是很累的,人的心其实是很苦很苦的!
这是家乡的夜景,冷冷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,村庄静悄悄的笼照在月光下,安详而充满神秘,令我神往。这是我画中的“家”,是我心中的“家”,也是我永远回不去的“家”。
多年来心中积累了很多话,一直想说出来,今天终于说了些出来了,如释重负。画面和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点往事和感受,记录了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,也记住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曾经善待过我们的农民。今天国家富强了,当我们回首,曾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付出时,一切便也释然了。
刚插队时村口有一座破旧的木桥,是村里通向外面世界的主要通道。走在晃晃悠悠的木桥上脚下还吱吱作响,桥板上坑坑洼洼的很是沧桑。村里人家的婚丧嫁娶,挑米辗稻,进出村庄都从桥上过。多年来这座桥承载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和村里人的辛酸苦辣,多年来这座桥也见证了村里的人世沧桑和时事变迁。
后来这座木桥因实在不堪重负被拆了,修了座水泥桥。
那时我们插队在苏北里下河地区,在大运河的东面,因地势低洼,故称里下河。那里河网密布,交通运输主要是靠人撑的木船,我们当初来时就是生产队用木船把我们撑到了庄子上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那里还很贫穷,社员住的都是茅草顶的土坯房。我们来后队里也给我们盖了一间土坯房,但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,在当时这就是比较好的房子了,称为“四角硬”。
队里的社员对我们都很好,他们为人很善良,那时每家的口粮都不够,而我们又不注意节约,常到青黄不接时没吃的了,我们常会向家前屋后的借米借油,尽管那时他们是一家几口也缺吃少穿的,但是仍然会借给我们一、二斤米,小半碗油。这些现在几乎是谁都没眼看的东西,但是在那时这几乎就是在借命啊!至今想来眼框都会湿的。
多少年了,忘不了他们对我们的宽容,忘不了他们对我们的照顾,也忘不了他们吵架时的那种互不相让、上房揭瓦的气势。他们吃苦耐劳,敢做敢当,敢吵敢闹、敢恨敢爱……这就是我们苏北的农民,也许这也是中国广大农民的缩影。
我们刚来时,村里的小店是在当时的大队部里,这里是全村庄最好的砖墙瓦房四合院,店里卖些农民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和小的农具,如要买比较好的东西,大多要上临泽镇了。记得我常在这里买“山芋干子酒”和八分钱一包的“经济”香烟。那时当地最好的香烟可能就是“大铁桥”了。那年有个在子婴河插队的知青到我们这来玩,吃饭时他说到:他和生产队里的社员喝过“钉子酒”,就是一瓶酒一个杯子一个锈钉子,每喝一口酒,就把钉子在嘴里吮吸一遍,喝酒没有菜,就把锈钉子的味道当下酒菜了。这还真没听说过,不过在那个年代,这种事也是有可能的。小店晚上点的是罩子灯,比一般人家亮多了,所以晚上常有人在这里抽着旱烟三三两两地说闲话。那年月抽的也就是干树叶摻和着烟叶,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,他们说这是“扯焉子”,也就是混时间的意思。小店到了晚上是要上门板的,门板上还依稀可见西一,西二,东一等毛笔字。
后来村东头盖了供销合作社小店就没有了。
那时庄子上有两个生产队是女知青,她们比男知青多个苦活就是插秧,好像四、五月里就要开始插秧,天不亮就要起来烧早饭,等一切忙定天也亮了,斗笠一戴裤腿卷的高高的就下水田了,从早晨下田插秧直到天黑收工,几乎一整天都在水田里弯着腰插秧,遇到刮风下雨,就用一块塑料布往身上一披就是雨衣了。水田里常有蚂蟥,那是一种吸血的虫子,叮在腿上就下不来,等发现了把它拽下来了,伤口还会继续流血,要好大一会儿才会慢慢止住。所以只要下水田干活,都要时不时的看看自己的腿。一天插秧下来,天黑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,她们说腰好像要断了。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种田是很辛苦很辛苦的。那时我们队里有五百多田,大多是种双季稻的,真是一年忙到头,春节小年刚过就开始犁田、耙田、育秧、插秧、薅草,然后收割、脱粒、晒稻、翻场。再然后晚稻从七月份开始,又把早稻的农活再重复一遍,直到十二月晚稻上场。冬天还要外出上大型(大型水利工程)挑河工,下河罱河泥、挖草粪塘、开沟挖墒等等等等,接着就过春节,这才能歇几天。小年刚过又开始犁田……。年复一年,农民们整年忙的都没时间看病,当然也是没钱看病。村上虽有合作医疗,但也就是看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,那年头缺医少药,所以农民们小病就扛,大病就拖。农忙时刚收割的稻子一上场就要连夜打稻脱粒,一天睡不了几小时,连续几天下来,人都累的迷迷糊糊的,为抢时间做饭,就胡乱的打一锅稀面糊吃(青黄不接时有点面粉打面糊吃就很好了),撒点盐搅和搅和喝上两碗,碗一丢立马出门继续干活,晚上回来已累的不想动了,盛点锅里中午剩下的面糊吃,盛到快见底时才发现锅里有东西,捞起来一看是一条长长的抹布。
我们知青这一代人,有了在农村历练的这碗酒垫底,在以后的工作中,什么苦事难事我们也没怕过。我们继承了农民吃苦耐劳的品质,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地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。在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知青的血染成的。
牛在农村是主要劳动力,耕田钯地,辗稻打场都少不了它,所以社员们对它们呵护有加。冬天牛在牛屋里好吃好喝,天冷了还烧火取暖,还有人睡在那里陪着它,夜里还要喂料,还三天两头地往牛嘴里灌香油,很是令人嫉妒。冬天冷的时候我们还会钻到牛屋里沾牛的光,那里暖和。
那年月农民要操心锅里的米,还要操心锅下的烧草,锅上锅下少一样都要挨饿。我们到了队里,烧草成了问题,我们锅上有米(当时好像国家供应知青半年的粮食),但锅下没烧的,生产队便决定我们烧牛草。所谓牛草就是稻草,是牛的饲料,那时牛过冬直到来年的早稻上场,饲料全靠牛屋前的大草堆了。我们烧稻草就是烧牛的饲料。那时我们还不知节约,常拔很多的牛草回来烧热水洗脸泡脚,而社员们只是用大灶上靠大锅边的小铁罐子里的那一点热水(当地称之为“罈罐”),罈罐里的热水是烧饭时温热的。社员们是很少专门烧热水用的。我们那时随意的烧牛草,太奢侈了。现在想来还很是慚愧。
我们插队时村上还没有通电,社员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墨水瓶里面灌点媒油或柴油,上面有个园的铁片盖住瓶口,园片中穿个小铁管,中间再穿根自己捻的粗点的棉线做灯芯,这就是灯了,栓根绳子挂在墙上,蚕豆大小的火头还冒着黑烟,灯点的时间长了,第二天起来鼻孔里都是黑的。条件好的人家,晚上点有玻璃罩子的媒油灯,这种灯亮而且不冒黑烟。那时我们点的就是罩子灯,我晚上画画所以睡的晚,一晚上要点一灯煤油是用二个鸡蛋换的。
那个时候农村的交通落后,汽车很少,等班车也没有个准头,好在那时有二轮车,也就是二八永久自行车后面货架上捆绑一块长木板,可以带二个人,倒也方便。骑车人技术很高,等后面二个人坐好后,大喊一声“别动了”,推着车就跑,然后一脚狠蹬一下地面迅速抬腿绕过大杠坐稳。技术娴熟,整套动作一气呵成,令人叹服。
半个世纪前,运河大堤的公路上跑的公共汽车,那时车顶上装好货后,就用大网子罩住拴结实了,才开车。有时开到半路上,发动机熄火了,司机就要下车,拿出根铁的摇把插进发动机里摇,司机摇累了机器还不响,这时就有乘客下车来自告奋勇地接着摇,直到汽车发动。车上的乘客也司空见惯,也没什么怨言。那时的人很宽容。换到现在,又是投诉又是赔偿的,现在的人反倒不宽容了。由于当时的路面状况不是很好,好车子跑几年,也就成这样了。
画面中画的是邻县高邮的界首镇,这是大运河边的一个镇子,因地处高邮、宝应、金湖三县交界而得名界首。这个镇子在大运河的河堤旁,也是一个千年古镇。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界首镇离我们双琚较远,插队十年我只去过两、三次,感觉很破旧,好像就一条街。因为界首在运河边,所以界首码头也是大运河里南来北往重要的水陆码头。
大运河中的客货混装的小班轮,主要作些短途的客运和货运。当然也可以直接抵达扬州港或镇江港。票价比汽车便宜。
这是家乡的夜景,冷冷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,村庄静悄悄的笼照在月光下,安详而充满神秘,令我神往。这是我画中的“家”,是我心中的“家”,也是我永远回不去的“家”。
多年来心中积累了很多话,一直想说出来,今天终于说了些出来了,如释重负。画面和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点往事和感受,记录了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,也记住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曾经善待过我们的农民。今天国家富强了,当我们回首,曾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付出时,一切便也释然了。
这是当时运河里的小火轮,它能拖着三、五条或更多的那种木头的货船,在运河里跑运输。我们当时就是坐着几条货船,由小火轮把我们从南京拖到宝应的氾水镇,好像再分到小船上拖到夏集,然后再由各大队的船带走直到生产队的。五十年前的事了,也只能依稀记得了。
我们刚到农村,我们对一切都感到新鲜,但是对一切又很无知。当时生产队是撑船把我们接回的,船快到庄子时,只见远处的天底下,是一大片灰蒙蒙的草屋,环顾四周一片沧凉,河两边一眼望去很远的天边有点树影,周围一片死寂,只有船在水中前进时“哗”“哗”的划水声。心中顿生悲凉。到了庄子后,看到社员们穿着打了很多补钉的衣服,再看着那片低矮的草屋,不禁困惑。还以为像电影中的一样,社员们都穿着新衣服,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……。和想像中相差太大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自己一直很徬徨、迷茫。我是属于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那部分人,所以平时只知道埋头干活。干着干着“一不小心”干成了个“学毛选积极分子”,还和我们庄子上的另一个女知青,一同参加了“宝应县知识青年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,开了这次大会后,“长了见识”,学习了“新思想”,回村后也大概地知道了,今后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在这片贫脊的土地上。
刚来到苏北平原,田里还有大风车。风车转动带动水车翻水灌田,大风车转动时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,我们队好像有两架大风车,那时生产队里还有人踩水车灌田的,人站在水车上踩,那是要点技巧的,不会踩就会就掉下去。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五百多亩田,是全大队最多的,最远的是凌田,人走到田里干活几乎看不到庄子,所以我们那时下凌田干活都要带中饭,中午不回家。凌田做活是很苦的,尤其是夏季稻田薅草,连找块阴影休息一下的地方都没有,任由毒辣的日头爆晒。一个夏天能脱皮两三次。一马平川的苏北平原就是在冬天刮起北风来也是肆无忌惮、无遮无挡、凛冽刺骨。
那时农民的生活的很苦,口粮不够吃,干活时每天可以烧顿干饭,如遇雨天不上工,一天最多也就吃二顿稀饭。那时要上交国家一定数量的粮食称之为“公粮”。上交的公粮都是上好的稻子、麦子,而那些颗粒不饱满的不好的我们称为“下脚稻”的粮食,则留下分给社员作口粮了。中国的农民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忍辱负重、辛苦劳作用自己的勤劳和付出支撑起了整个国家。
我们家共五个人,都是同班同学,就组成了一家。那时刚插队,我们吃粮国家还是有保证的,有时吃不了还有节余,日子长了余粮也就多了,社员粮食不够吃,我们粮食还多了不少,于是就想出了餿主意:卖粮换钱。这在当时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,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全国人民都吃不饱,你们胆敢卖粮!当时我们撑了条船装了两大筐白米出了庄子,直奔临泽(是十多里外的一个镇子),后来队长顺着大河堤一路追来才把我们截住。后来是大队,小队对我们教育,再后来粮食怎么处理的我记不得了,只是记得后来没处理我们。
那时我们年轻,太不懂事,地里的活干不好,却还相互打架,偷鸡摸狗。当时村上农民还很贫穷,经济上仅靠年底队里的一点分红,是远远不够家里一年的生活开支的,柴米油盐、日常用度。所以,一般农户还指望家里的鸡下蛋,拿到村头合作社里换点媒油、换点盐、换点其它生活用品。但是这些下蛋的鸡却给这些“挨千刀”的知青偷了。他们对我们是痛恨有加。那时我们偷鸡前就要烧好了一锅水,鸡被夹在棉袄中带回来后,立马热水烫、拔毛、开膛破肚、下锅大约十分钟左右拿出来,这时鸡肉最嫩,再煮就老了。然后麻利地切鸡,开吃,也就几分钟桌上就剩一堆骨头了,报纸一包扔了。出门后像没事人似的。我们以为没人知道,其实社员们在田里干活时就知道到了,知青家烟囱冒烟了,不知哪家的鸡又没了。因为上工时庄子上是不会冒烟的。我们只是掩耳盗铃罢了。为此社员从小队闹到大队,而那时大、小队干部也是多偏袒我们,所以也就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,我们真的很深很深地伤害了这些贫苦的农民。可是当我们有困难时,社员们仍然会帮助我们。队里派农活时还是会把轻活派给我们。他们的大度和宽容至今都令我们无地自容。
今晚邻村大李庄放电影。这消息不径而走,大家听说后都很兴奋。到下午时庄子上各个队的社员都无心干活了,巴望着太阳早点落下去。我们干脆提早收工,匆匆回家,赶紧挑水、淘米、点火做饭,今晚要烧干饭,因为来回要走十几里路呢。就着一点腌菜吃完饭了,门一关拔腿就走。门也没锁,其实锁不锁都是无所谓的,那会儿民风好。出了庄子看见往大李方向的田间小路上早有人急急地往前赶了。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,一年能看场电影已是很好的事了。平常哪个村子放电影,周围十里八乡的社员都要去看的,人们都穿的干干净净的,大姑娘小媳妇们是要打扮一下的。天擦黑我们才赶到,电影已开场了。只见幕布前后都是人,其实前面看后面看都是差不多的。那会儿还没通电,放电影的都要自带发电机的。只听得远处的船上发电机“嗵、嗵、嗵”的响,一根粗皮线连到一张桌子上的放映机,桌腿上绑根竹竿,上面挑个小灯泡照着放映机,桌边还围着一圈小孩,后面还有张桌子,另一个人在倒片。前面的银幕是二根粗长的竹竿埋在地下,银幕就栓在两根竹竿中间绷平,竹竿上捆个大喇叭。我们就在银幕后席地而坐。今晚放的是“上甘岭”和“永不消失的电波”两部片子。那时革命战争片子是很收欢迎的。当银幕上的新闻片头结束正片开始后,吵杂的场子顿时安静下来了,人们都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看着银幕,在电影播放中,有时大喇叭还会插播一下生产队领导班子开会的通知。人们对这并不在意,大家的情绪随着电影里情节的起伏,时而高兴时而稀嘘。随着电影的播放,夜已渐深。电影放完已是快十一点了,散场后人们各自回了。漆黑的夜晚,远处田里不时有电筒的灯光,忽闪忽闪的像天上的星星,大人小孩意犹味尽地谈着电影里的情节,嘻笑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。
那种来回跑十几里路看电影的感觉,那种单纯而简单的快乐,现在再也没有了!
有年冬天特别冷,春节快要到了,我因没钱就不回家了。我们家的两个知青准备回南京过年,那时我们回家都要带点年货的,队里养的鱼或田里种的茨菇。那年他们准备了两纸箱子鸡蛋,这个在城市里也是稀罕货。好像是因为雨雪天,汽车不通,他们便到邻县的沙沟镇,准备坐船到镇江,再在镇江坐火车到家。那时交通太不方便了。他们到了沙沟,没想到天太冷了大河结冰,船也不通了,想回来路也不通,结果他们在沙沟那个小码头窝了三天,因没钱吃饭,就找了人家帮忙煮鸡蛋充饥。后来总算到南京了,可能年货鸡蛋也吃的差不多了。
这是那个年代内河里常见的小班轮,也是客货混装,沙沟码头在那时也停靠这种小班轮。如果那年沙沟水面没冻住,他二人就坐这小班轮到镇江了。
我们里下河地区,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,这一带的老战士很多,我们那时都喊他们为老革命。他们大多是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,胜利后也许因为没有文化或其他原因,又回到了家乡。那年头国家也很困难,还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些老兵。当时他们还很穷。每到年关,有很多人都是要出去跑年(要饭)的。所以每到过年,各村大,小队干部都很紧张,每年按上面指示要制止老革命跑年。我们庄子上就有一个老战士,我们叫他老艮,他曾和我们说:当年新四军打兴化城,架梯攻城,被敌人剁下来的手能用箩筐装。可见当时战争的残酷。每到过年大队里再怎么困难,也要给老艮一点米、油和几斤肉,让他过个饱年。
我们干活时间长了,就想到临泽镇子上去玩玩。吃顿饭解解馋。我们一般早晨起来吃过早饭后,要等到社员们都下田了,我们才出门。那时庄子里已静悄悄的了,颇有点“鬼鬼祟祟”的感觉。我们出了庄子上大堤,过了匡庄就顺着河堤往前走,大约十里左右,就远远的看见河上有个没有栏杆的木桥,桥下停了很多大小船只,不断的有人在跳板上来来去去的上货下货。过了木桥便进了镇子。这是个千年古镇,历史上曾是高邮县的三大古镇之一。镇里三街九巷,交通畅达。古来曾是商贸重镇。上世纪六,七十年代的临泽虽已无往日的繁华,但仍是这方园数十里的商业中心。镇里街面不宽,窄窄的街面中间一条青石板小路,两边是商铺,店家,日用百货,饭馆粮行,那时店家都是上门板的,跄在街边的门板上用毛笔写着数字。店里的柜台和墙上的立柜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花绿绿的商品。街面上人来人往,带草帽的、挑担扛包的等。这都是附近的农民来买东西或办事的,来去匆匆。这场景不禁使人想到电影“林家铺子”。玩了会儿几近中午,找家饭店吃饭,那时饭店里的地面大多是青砖铺地,打扫的干干净净的,店里几张四方桌,每边一个长条凳,落坐后,一个人去交款处点菜付钱,交完钱后,顺手在旁边柱子上的筷筒里抽几双筷子。菜上齐后,拿起筷子夹在腋窝里来回抽几下,算是楷过筷子了,然后就不客气啦。几瓶啤酒下肚饭菜一扫而空。吃过后再在镇子上逛逛,太阳西下时就回了。每次吃饭都少不了把饭店里的筷子、小勺子、小盘子吃回家。
这是常年在内河里跑运输的的水上人家,这些人长年以船为家,这种机动船也为临泽镇,沙沟镇,三垛镇等里下河地区的各个地方,运输日用百货和农用物资。那时公路交通不发达,路面状况不好。水运装载量大而且成本低。所以这些机动船是当时里下河地区的运输主力了。
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,田地里基本上也没什么活儿了,一年里也就这几天能闲下来。庄子上开始忙起来了,家里的女人忙着里里外外打扫,忙着准备过年的吃食,忙着洗洗涮涮,忙着锅瓢碗盏。有人家过年办喜事的,更是忙的不可开交,张家借桌子,李家借凳子,家前借碗,屋后借锅,日子过的再苦,年总是要好好过的。条件好点的人家小孩过年能穿件新衣裳,一般人家也就穿件干干净净的,补丁少点的衣服。姑娘家没新衣服的也总是要把头梳的光光的,脸洗的干干净净的再搽点雪花膏,别上几个漂亮的发卡,有的嘴上还会用红纸淡淡的抿一下。
每年春节庄子上都要组织演出,自从知青到后,我们便是演出的主力了,那时我们还演出了革命样板戏“沙家浜”,记得演主角的郭建光是我们大队星河生产队的知青。这些都已是过去的记忆了,那时我们在贫穷的苏北农村也有快乐的时候。
再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,过年每家都要舂糯米粉,还要赶在年前抢个好太阳把糯米粉晒干。所以每家都想赶紧把糯米粉舂好。那时我们队上只有一个对子,在生产队东头的一间大屋里。所谓对子,就是地上埋个石头窝窝,上面架个木头架子,支撑一根长木棍,对着石窝窝上面的木棍头上捆个一头大一头小的石头,小头正对石窝窝,木棍的另一头是人脚踩着一上一下,小石头就一上一下地砸进石窝窝里,把糯米砸碎,砸成米粉。对子是整天不停的,你家舂好他家接着舂,那几天晚上没事的社员也常到那里玩。屋里紧靠对子的墙上挂着一盏忽明忽亮的的小油灯,蚕豆大小灯头来回晃动冒着黑烟,屋里已有不少人了,紧靠对子的地上已有几个盛着泡好糯米的盆子,对子上一个人在踩着木棍一上一下的舂着糯米。屋外寒冬腊月,雪花点点,屋内人多暖烘烘的,微弱的灯光下谁也看不清谁,大家挤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的扯着闲篇,话语里夹杂着粗话和呛人的烟味,仿佛一年的辛苦全融化在这“咚”“咚”的舂米声和大人小孩的嘈杂声中。在半明半暗的油灯下,人堆里不时发出阵阵说笑声和低低的啜泣及骂声,在这里人们尽情地喧泄着一年来的坎坷和辛酸苦辣,人们心中积累了太多太多的东西,在这个晚上也毫无顾忌地流淌出来了……。 那几天我也总爱往那屋里钻,蜷缩在墙角的草堆里,听着对子一上一下有节奏的撞击声,听着粗声细语的说话声,感受着浓浓的年味,竟入梦乡…… 。
记得那时公社前面是一条泥巴的路,大路边是大会堂,当时好像是没门没窗的,里面也就是泥土地面上面摆着一些做工粗糙的长条凳子。那年头农村太穷了,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开开会就不错了。公社招开的“三干会”、“知青大会”等各种大小会议就是在大会堂招开的,这里还演出过夏集大队知青自己排演的舞剧“白毛女”。公社大路的右边是邮局,记得那时打长途电话到南京,要在公社邮局里等,等这边电话摇到南京,南京那边也要在新街口邮局等,等电话接通了再叫你到几号几号小间去接。那时通个长途电话太困难了,而今天是一部手机走天下。
明天是大年三十,中午时分,公社那条不宽的泥土路上,人少多了,苦了一年的农民也早早的歇了,都回家准备明天的年夜饭了,我被借到公社干的活也干完了,也该回家了。虽然明知回去也是一个人面对一间空空的茅草屋,家里已没米了,要借米,要洗涮多日不用的水缸,把水挑满,还要去捆烧的草,还要去买晚间点灯的油,还要……,还要……。虽然回家连菜也没有,但是家还是要回的,一个冷冷清清的家。我在公社早早地吃了中饭,就急急的上了潼河大堤往家赶,空旷的天空中偶有点点雪花飘下,大约走了个把小时,已能隐约看见灰蒙蒙天空下的庄子了,忽然又不想急着回家了,想一个人在这空旷的天地之间待着,体味这在路上的感觉,一种在不停地赶路的感觉。人在路上就有一种企盼,有一种幻想和期望。真的到家了,一切也就没有了。
人这辈子大约也是这样,在不停地赶路,“家”永远在前方不远的地方。有人回“家”可能只要几天,有的人回“家”可能要几年甚至一辈子……。人其实是很累的,人的心其实是很苦很苦的!
这是家乡的夜景,冷冷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,村庄静悄悄的笼照在月光下,安详而充满神秘,令我神往。这是我画中的“家”,是我心中的“家”,也是我永远回不去的“家”。
多年来心中积累了很多话,一直想说出来,今天终于说了些出来了,如释重负。画面和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点往事和感受,记录了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,也记住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曾经善待过我们的农民。今天国家富强了,当我们回首,曾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付出时,一切便也释然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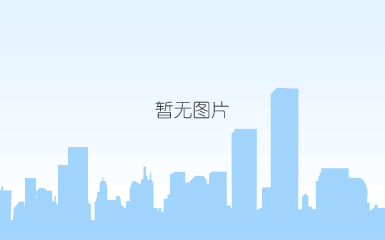
- 上一篇:七言绝句《别扬还冀》
- 下一篇:宝应古巷中的蒲松龄
| | 联系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 扬州拓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k8凯发的版权所有 k8凯发 copyright © 2010-2021
![]() k8凯发的技术支持:平邑在线
k8凯发的技术支持:平邑在线

